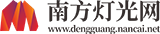丰年,瑞光
“小老鼠,上灯台 偷油吃,下不来 叫外婆,外婆不来 叽哩咕噜滚下来……”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一
青黄的麦田,暖风轻拂,黄灿灿的麦子慵懒着,像村口的老人躺在摇椅上,微闭着眼,透过朦胧的眼光看着自己青涩的后代。
田边那棵巨大的皂角树上,春暖花开。
“娘,俺们去哪儿吃饭。”“去侬大舅家。”母子间的对话行走着,向黄瓜藤里鬓边微白的几个老农传来几丝生气。我时常想起,那个偷拿外婆的钱去买玻璃弹珠的下午。
那是一个夕阳灿烂的下午,秋黄瓜青玉的面庞泛起阵阵白皙,道边的蚂蚁有序搬运着金粒般散落的果实。我躺在略有湿润的干草垛上,向南的风将秋黄瓜的清甘吹来,吹向我面前碌碌的蚂蚁,惊起我眼中乱飞的蜻蜓。蜻蜓们跳动着,是村东头每年来好几次的伶人们演着我看不懂的戏,于是我在秋风树影下的斑驳流年中,在社戏的叮叮当当中昏昏睡去。模糊着,几片光的映照和着风轻抚我的头发,像慈祥的外婆怜爱的看着我睡去。蜻蜓身下抽水井的锵锵锵,又如同夜晚总在眼前的扇子吹起的风声……
我在梦中遨游,无意识地走向家的方向。那白皮脱落的外墙,朽木的窗框前是那断了一只脚的桌子。桌子的左边,父亲拿着一个玻璃瓶子,里面酱料的颜色已模糊不清。父亲的对面,母亲一只手拿着大葱反复转动着,像在找什么,桌上一堆葱,地上半篮葱,那篮子里可爱的静静躺着的那些葱,自己藏起来的秘密也许被找到了吧。
我未曾理会他们,走向窗框左边石头砌成的楼梯,阳台上是一床红绿的被子。我穿过他,走向楼梯口对边的矮木椅子,坐下,看着夕阳。
“憋离房檐太近,一会儿下来吃饭。”“晓得咯。”
楼上湛蓝的天还未被镀上橙色,方方正正的蓝天,像外婆那蓝色的铁皮柜轮椅。
二
天上的鸟儿巡视,看向地上参差不齐的村庄与田地,他们发现蓬松的麦地像是农户们家中的枕头。那枕头偶尔有线突然蹦出来,像是蓬松的麦地上挥着锄头的农户。
田边,房子边,白色的大卡车和褐红色的拖拉机轰隆隆的呼啸,灰色的油烟和农户们的炊烟两条线似的缠在一起,到最后任谁也看不出来了。
那时农村不发达,老人活到七十便是常态,外公外婆却是分别八十,九十之高龄,是村内公认的“长寿夫妇”。在田间,房屋间数十年如一日的生活着。
他们就生活在这么一个方方正正的小天地里。她和外公一直住在村北的小房子里,每天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,偶有无话可说,就看着田边房前叽叽喳喳的麻雀一天天来,一天天走。
我对外婆的记忆,总是伴随着腌萝卜菜的味道。她和外公常常在方正的四合院中央拿上一个绿色大盆子,搓衣服一样刮着白色滚圆的萝卜。那白色的萝卜成了青色的腌萝卜条,又进到了我们和大舅,二舅三家嘴里。
晚上,兴奋的知了叫着,外婆在屋内房檐挂着的玉米下点着昏暗的油灯,灯前是一个棕色的大缸子,缸前是白色的脸盆,装着青绿的萝卜。
外公在世的时候,常常嫌弃外婆放的花椒多,外婆一边将盆子内的萝卜条放进缸里,一边将话夹在长息与笑中说出:“只有那样,才更加入味。”
知了睡了,外婆将盖子盖上,边上是不知入味了几年的山西陈醋。
外公做了几十年的饭,却在这点上不如外婆。外婆看似就是个糊涂的老太太,但她又好像什么道理都知道。
外公倒在了次年的倒春寒。
三
外公在皱纹中开怀笑着的照片成了黑白。从那以后,外婆就每年轮流在她的三个孩子家居住,每年在我家的时间最长。
我小时候经常发烧,诊所的老医生是个沉默寡言,老眼昏花的老头子。他总是手背一摸额头,就知道我们是什么病,吃哪种药。我们这些病人坐着的蓝色塑料椅子边上是堆放着种种药的柜子。我在椅子上坐着,看着吊瓶中的点滴滴滴下流。看着那老医生透明保温杯中黄色的茶,浮着的枸杞。看着他苍老的手拿着几撮药,方方正正的放进布包。
次天,我在蓝白色网格的被子中起来,烈日已正轮当空。
午饭基本是早上剩的,用蓝色的网罩子盖着,三盘菜上飘着绿色的大头苍蝇。边上是同样蓝色的苍蝇拍,好像整年油腻腻的。
放着各种牌子洗发水,沐浴露的架子左边,错综复杂的水管右边,一盘挂在水龙头上的镜子看着我。
我看着他,看他眼中我嘴里摇摇晃晃的牙。还是与以往一样拔不掉,凉丝丝的。
从学校回家的门口有一棵皂角树,我与几个村里的同龄人经常撅着屁股趴在地上,兜里是几十个村口杂货铺的玻璃弹子。拇指一盘,食指卡在拇指后面,三根指头一立,食指一弹。在弹指间我们就与玻璃弹珠消磨了整个下午。当空气中弥漫着的光已经泛黄到可以透过玻璃弹子看到满眼的金色,母亲让我们回家前把皂角树下的皂角捡起的吆喝已经穿透而来。我们惊慌地胡乱捡起几颗绿色的皂角,将豆大的蚂蚁弹到已经枯黄的皂角上去。几个还没庄稼高的孩子一边在路上跑着,一边将玻璃弹子和皂角塞进小小的兜中,背对夕阳奔跑。
皂角汁液洗出来的被子挂在阳台上,有着阳光温暖的气味,香香的。
这个夕阳和以往不一样,母亲从高高的门框踏过:“三孩儿,你姥娘来了,赶紧回家吧。”
我绕了房子一圈,看到了大舅家的蓝皮卡车,边上是随意堆放的玉米。外婆被父母搀扶着,摇摇晃晃走下来。
外婆来的时候,母亲总喜欢做红薯叶面条,我不喜欢吃叶子,就把叶子挑出来压在碗里,或是故意不把汤喝完,把叶子藏在汤里。每个晚上,大家都吃完的时候母亲却总是又从锅里盛一碗面条,这个点,面早就烂了啊。
母亲让我把面条送到外婆房里,叮嘱我看着她吃完,再把碗端回厨房。
外婆年纪越来越大,老忘事。有时她看着我把碗放在她边上,再看着我匆匆出去玩,面却总了吃。
“娘,我得牙不舒服。”“该换牙了吧,憋老用手碰它。”
四
父母总在忙农活,特别是玉米丰收的季节。此时大姐二姐都会回来帮忙。
二姐在外婆家长大,她和外婆关系最好。二姐的小名叫迎戏,是外婆起的。老家人都喜欢在村东头看戏,外婆希望她像戏曲一样有宝贵的文化底子,受人欢迎。
我曾在二姐手中看过外婆年轻时的照片:她在金灿灿的麦田中一身绿色的军装,帽子正中是一颗红星,红星的两侧是整整齐齐的麻花辫与调皮的碎发。外婆的年轻时的脸在记忆中给我造成了极深的印象:两条黛眉如同远山一般,温柔的眸子像是平静的秋水,小麦色的脸庞笑的很柔和,眼中是青春的光。
风华在灿烂和时间中死去,活下来的是田亩一样的皱纹。
一天天过去,当到了夏至。外婆的腿脚也不利索了,于是父亲找二舅焊接了一个蓝色的铁皮柜做成轮椅。农忙的秋收,妈妈将照顾外婆的重任交在我身上。倒尿桶是我最讨厌的事情。我左手捏着鼻子,屏息凝神,右手提着尿痛,手臂的幅度大幅向前倾。每次倒完,手洗了一次又一次,还仍不敢触摸什么。
因此,我也讨厌外婆。
外婆总喜欢在清晨散步。于是我推着那个轮椅与外婆,只是顺着随意的节奏走着。一老一小无形的隔阂,在田埂边的道路上无言的行走着。
那个铁皮盒子能装东西,于是我在一个中午趁外婆午睡的时候打开了盒子,在铁皮柜的上层发现了外婆的钱。
它们在一个布包里,布包在剪刀,拖鞋,外公的遗照中间。那张最旧,面值最小的毛票成了几十颗弹珠。玻璃弹子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瑞光看着太阳,而我看着它。
我拿着弹子在田间漫步,田边是炸开的西瓜和半人高的麦穗。我最终坐在一颗高大的槐树下面,一个推起来的田埂上面,背靠小麦,看着整个村子与远方的远山,看着方方正正的蓝天,白云。
五
我后来又拿过几次外婆的钱,直到我一天在家中漫游,无意中看到外婆坐在墙角,装钱的手绢铺在腿上,边上的铁皮柜子门户大开。于是我躲在屋檐下,看着外婆一遍又一遍数着钱,嘴里默数着什么。我看见外婆将它们包好,放在原处,好像什么都没发生。
是不是外婆早已忘了里面有多少钱?
这个晚上,母亲照常把面条端给我,我照常送往外婆的房间,但这次,我没有溜走。而是看着外婆把饭吃完。外婆脸上的皱纹真的好多,张嘴时一条条沟壑抖动着,吞咽时嘴里还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她咀嚼时脸上的皱纹总会偏向左侧,那是因为她只剩三颗牙导致的。
我看着,小手握的紧紧的,攥得通红,指甲都仿佛要嵌进肉里,水珠堆积着,一粒一粒滚下来,温热的泪水落在我的手背,落在我和外婆的心里。
外婆停下来,将面局促地放回桌子上,颤巍巍的身子伸出颤巍巍的手,颤巍巍的将我抱住怀中。她眼里得温柔从来就不像她的风华,从来未曾消失过
“哎呦,这是咋嘞,莫哭莫哭,有外婆在。”
门口满尘的瓷观音像躲在桌上两束兰花中间,看似面无表情的偷听着。敞开的门前是家里温顺的大黄狗,惰惰地趴在地上,短短的尾巴随风摇曳,听着不懂的对话,懒懒着看着眉间柔和的观音像。
我将外婆的面碗收回洗手盆,一手端碗,一手拿着抹布旋转。当我将外婆的碗放在旁边,我的牙却忽然的一痛。
带着血丝,方才被我咬的紧紧的后槽牙,就这么落了下来。
我盯着它许久,往房顶上一扔。
六
秋后的那个冬天越来越冷了,外婆被送往那辆大卡车,被送往了二舅家过年。外婆的日常用品,随同那个铁皮盒子轮椅一同送往了二舅家。
小年前一共下了两场雪,气温稍有回温。元宵节前后却异常寒冷,气温骤降。原先金黄的小麦苗被冻伤了不少。槐树,皂角树默默伫立,逐渐干枯,那群经常来偷吃的麻雀不见了,只剩天中的孤鸦在凄厉的喊叫。
外婆没有熬过那个冬天。
两年前,外公也在这个小地方盍然长眠。
外婆去世的时候已经是九十出头了,按村里的规矩,是喜丧。锣鼓的呐喊在舅舅家响了几个时辰。丧事正中间的遗像温柔,慈祥的笑着,像是从未离去过。遗像边的两幅挽联镇静的坐着,偶有的浮动像孩童坐在椅子上调皮的甩腿。
也许外婆也在看着,看着我看向她,看着我看向她周围的“寿终德长在”“身去音容存”。欣慰的看着我闭上眼忍着泪。因为我感到,在寒冬中忽的有一丝暖风,颤巍巍地抱着我。
七
如春,麦苗褪去了冻伤的芽尖。今年由于两场雪的滋润,长势很好。
后来,大舅经常给我家送腌萝卜菜,还是一样的花椒味很重。
妈妈整理外婆的遗物,外婆将那个铁皮柜轮椅留给了我,它从大舅家又运了回来。
打开了柜子,难以想象那个方方正正的柜子容得下如此多的东西:剪子,鞋子,毯子,画片,衣服,裤子,镜子,篮子,扇子……
那个手绢包裹的钱依然留在原处,它边上的朋友加了一幅外婆的遗照。照片上的她和外公的遗照依偎在一起,恍惚着,我又看见了他们年轻时的灿烂与炯炯的目光。
那个柜子太小,甚至不如我的一个桌柜。那个柜子太大,仿佛装下了外婆的整个人生。
晚上,是许久未见的雨,纤细着,绵绵的落下。
八
思绪流转,回忆归来。
我向母亲将这一件件事说出,已是多年。
母亲对我说,那个冬天很冷,北风很大,许多村中的老人和村口的老树都没熬过。但那些老树死去时,天然的草木灰与瑞雪滋润着麦苗。那是一个丰年。
外婆年事已高,难以保暖。她当时一直想给外婆买个电热毯铺在床上,但秋收的季节很忙,常常忘记,后来便也不需要,忘怀了。现在每次想起来都会遗憾。
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。
那棵老槐树也断了,但残破的树桩子里,又抽出新的芽来。
我跑到那棵皂角树下,放下了玻璃弹子,只是看着繁茂的枝丫。
有不少瑞光,透过叶来照在我的头发上。
年年岁岁,岁岁年年。我承载家乡回忆在时光江河长驶不息。青春的记忆如那抽出的新芽,心如花木,向阳而生。年年的瑞光中,瑞雪中,我带上外婆的慈祥望向下一个丰年。
——2023.2.5 20:11于家中(观 向着明亮那方——外婆的铁皮柜轮椅所改)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bangumi/play/ep518980?theme=movie&spm_id_from=333.337.0.0
(《向着明亮那方》B站网址)
标签:
为您推荐
广告
- 丰年,瑞光
- 当前观点:问道手游怎么在电脑上玩-PC版安装教程_问道手游怎么在电脑上玩
- 4月北京新房市场如何?共产房全面降温 城区8万+项目成交逆涨-世界时快讯
- 世界动态:个人所得税是多少个点_个人所得税如何计算
- 【环球快播报】更健全、更高效、更便利 上海推出工程建设领域20项优化措施
- 天天速读:国家能源局:加快能源法立法进程 研究起草能源监管条例
- 酒驾卡口设法调头 周村交警依法查处一无证醉驾人员 每日热讯
- 安徽一对祖孙离奇失联10天,已抽干两个水塘排查
- 向美而生、与美同行!普陀这里的“城市美育日”系列活动精彩纷呈→ 全球今热点
- 彻底不怕“杀后台”!一加Ace 2原神定制版搭载18GB豪华内存 全球热资讯
- 雪人股份:4月11日融资买入378.37万元,融资融券余额4.04亿元
- 当前动态: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化总体组、专家咨询组全体会议召开
- 板凳发力!老鹰替补半场高效贡献35分 今日看点
- 华瓷股份董秘回复:股东信息请查阅公司定期报告 世界报道
- 3月CPI同比上涨0.7%
- 叫做和叫作的区别举例_叫做和叫作的区别
- 当前时讯:用AI“复活”亲人需看到背后的担忧
- 醪糟汤圆的做法_醪糟的做法
- 焦点热门:未来7天合肥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最高气温31℃
- 官方:雷丁主教练保罗-因斯下课_环球观焦点
- 1云南能投(002053.SZ)发预增,一季度净利润1.68亿元-1.85亿元,同比增长30.65%-43.87%|快消息
- 2最新快讯!【ES三周年】一文弄懂css权重
- 3传文化、送温暖!这群红领巾变身社区“小主人”
- 4当前短讯!镜花缘传奇主题曲周艳泓_镜花缘传奇主题曲
- 5天天热消息:享道出行泰安、济南难叫车,品牌回应
- 6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与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签署合作协议,共研数据交易价格形成机制
- 7恶作剧?更换图标后,马斯克又给推特“改名”
- 8河化股份:银亿集团的重整工作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之中
- 9天天精选!考辛斯我仍是联盟第三好的中锋 约基奇三连MVP考辛斯我不能苟同这将让他进入GOAT的谈论范围(今日/头条)
- 10【天天热闻】【我为群众办实事】三亚吉阳警方:凌晨2点,民警将寻回的手机交到游客手中
广告
- 途经北京铁路京广高铁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|全球速讯
- 沪深交易所主板注册制首批企业上市 带来数个利好消息 世界播资讯
- * 2月充会员只有28天,爱奇艺遭消费者质疑
- 环球播报:金融管理专业自考本科好考吗?
- 每日热闻!四川自贡中考满分作文:期待啊,我的高中生活 包头中考满分作文
- 美股盈利预期不断恶化! 科技股“清算时刻”即将到来?
- 视频解决方案提供商一览科技正式入驻京东 开启京东逛频道达人商单计划|全球今亮点
- 高铁“随心坐”来了,山东首推399元环游套票-世界播资讯
- 热点聚焦:湖南省消保委发布消费提示:教你规避二手房交易纠纷
- 建行信用卡分期后可以提前一次性还清吗-建行信用卡分期怎么办理 全球快讯
- banner设计是什么_Banner设计是什么意思
- 驱蚊液能上飞机么? 焦点消息
- 80岁老人生日礼物送什么好
- 全球视点!东部战区联合精确打击模拟动画公布具体详细内容是什么
- 盘点一些经典的绣球花品种 环球快资讯
- 天目湖最新公告:上半年净亏损5368.08万元 同比盈转亏
- 法国马赛一栋建筑物倒塌 已致5人受伤
- Chovy喊话Faker,这次该我赢了,管泽元全力支持Gen战队
- 英语同步听力七年级下册_关于英语同步听力七年级下册的简介_世界新要闻
- 亲沙乐土 自然生长 当前视讯